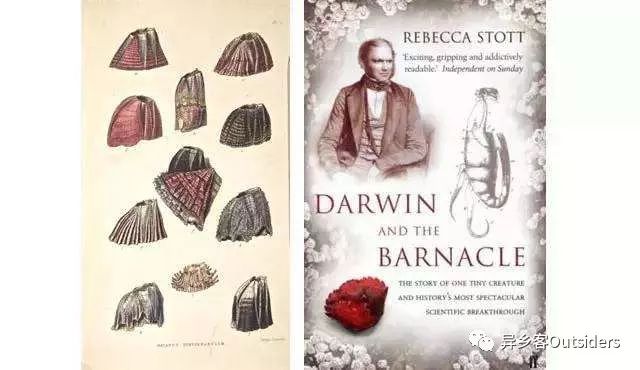| 牛津论战:进化论与神创论的首次激烈碰撞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进化论被推翻的证据是什么 › 牛津论战:进化论与神创论的首次激烈碰撞 |
牛津论战:进化论与神创论的首次激烈碰撞
|
现在已经知道伟大的开尔文计算结果是错误的,他忽略了地球内部放射性元素的作用,所以低估了地球冷却的时间,同时也大大低估了地球的年龄。 更严酷的批评来自哲学界和宗教界,他们指进化论是“粗野的哲学”和“肮脏的福音”,并把进过教会学校的达尔文比喻为一个“魔鬼牧师”,甚至当成是“欧洲最危险的人”。重压之下,以至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禁止借阅此书。 一时间风萧萧兮易水寒。 也有相当一批教会人员站出来支持达尔文,不过他们采取的是和稀泥的调和手法。这种理论在美国特别流行,他们认为进化论与上帝并不冲突,正是上帝创造了能够自我发展的原始生命形式,甚至进化的策略也是上帝制定好了的,这样一来,进化论就成了第二因,与上帝互不侵犯。而且,这样一搞,上帝反而轻松了许多,他不必一个一个费心费神地去制造万种生灵了,他只需要制定一个生物发生和进化的原则就行了。可能有的时候还插手修改一下进化过程中出现的小错误,比如搞死一大批恐龙之类的小事情。 而在保守的英国,受过正统教育的牧师们仍然出离愤怒,因为《物种起源》是对《圣经》中描述的过程的全盘否定。这样一搞大家就不相信上帝了,而一旦人们开始怀疑《圣经》,那人生的一切都将失去意义。在虔诚的教士们看来,生物进化理论将颠覆整个世界的伦理与道德。 在这种气氛下,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已不可避免。 《物种起源》刚一出版,赫胥黎就写论文宣传和支持达尔文,并利用在皇家研究院演讲的机会公开支持进化论。而此时另一批人,比如威尔福伯斯(Samuel Wilberforce)已经开始和很多人一道写文章攻击达尔文了,动物学家欧文(Richard Owen)更是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论文对达尔文大加鞭挞,在剑桥哲学学会上对达尔文众口交攻,唾沫喷了一会场。达尔文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欧文虽然长得很丑而且生性冷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著名的动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他自小痴迷于动物解剖,并为此而享有盛名,一共发表了六百多篇解剖学论文,其学术成就与名重一时的居维叶有的一拼。正是他发现了始祖鸟,也正是他把一种大家都没见过的化石命名为“恐龙”,出版有经典巨著《论脊椎动物解剖学》及其他一大批专业作品。可惜这个人的道德品质并不能如其学术成就那样让人尊敬,经常做一些迫害同事及偷窃别人研究成果的工作,大大削弱了他作为一个重要学者的影响力。
但对他影响更大的,恐怕还是与赫胥黎的论战。 那时,赫胥黎开始实践自己要为达尔文做斗犬的诺言,他开始针对性地写反驳文章,但这种缺乏当面交锋的论战缺少火花与激情,很快被人遗忘。 正面交锋的机会终于来了,1860年6月27日,英国科学促进会年会在牛津召开,开会第二天,在动植物组分会场上,赫胥黎开始对欧文发难。因为欧文声称,通过解剖学研究发现,大猩猩的大脑与人的大脑之间的差别很大,超过了大猩猩与其他动物的差别,也就是说,不应该把万灵之长的人和这些低等动物放到平起平坐的位子上加以比较。这一说法令赫胥黎很不开心,赫胥黎相信猩脑与人脑之间的差距不大,是两个非常接近的物种,这一观点支持达尔文的理论。 所以赫胥黎接下来毫不客气地回击了欧文,这个家伙用非常不礼貌的语气嘲笑欧文说:“即使我能证明大猩猩是他们的祖先,他们也不会害怕。” 这次会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争斗仍在继续。欧文提出了一个解剖学上的证据来证明人的优越性,即人的大脑中有一个重要的结构——小小的海马状的回转部位,称为海马回;而在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脑中则没有这个结构。这一区别可以充分说明人的独特性,并证明人与猿之间在结构上不存在所谓连续性。所以人不是猿进化而来的产物,人类大可为此而感到骄傲。 赫胥黎正在写作专著《人在自然中位置的依据》,他有足够强大的资料表明,所有的猿都有海马回,人脑和猿脑之间存在明显的连续性。这场争论曾引起全英国的关注,后来终以赫胥黎获得全面胜利而告终。当有人劝赫胥黎对欧文进一步攻击以把他的理论全部打倒时,赫胥黎感叹说:“我们的生命太短了,不能将已经杀掉的再杀一遍。” 其实这两个人一直就是宿敌,正是赫胥黎把欧文从英国动物学会和皇家学会委员会中用投票的方式挤了出去。后来欧文只好放弃科研工作,去大英博物馆自然史部上班,并为创建伦敦自然史博物馆付出了大量努力。在做好博物馆工作的同时,他没有忘记对老对手的嘲笑和报复,他四处游说批驳达尔文的理论,并强烈反对为达尔文和赫胥黎修建雕像。当自然博物馆不得不摆上这两个人的雕像时,无可奈何的欧文只好在雕像的摆放上做了点手脚。在他的地盘上他有这个权力,他把自己的雕像放在博物馆大厅最显要的位置,而达尔文和赫胥黎的雕像则被摆在博物馆开设的咖啡店里,整天脸色严肃地看着那些啃面包喝咖啡的客人们。
这次会议上,欧文只一个回合就很快败下阵来。第二个出场的就是牛津教区主教威尔伯福斯,因为善于论辩,人称外号“油滑的山姆”。 在会前,欧文就和主教商议好,要借这次机会把生物进化理论彻底从生物学界清除出去。这个消息早就传了出去,温和的达尔文可能预见到了这场争吵,所以没有出席会议。据传本来赫胥黎也不想出席此次会议的,他怕受到那些虔诚的教士们无休止的攻击,是在胡克的劝说下才披挂出征的。 科学大会还在继续。 会议进行到第四天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听众赶来听动植物组的讨论。这些人大致都是有目的而来的,他们估计到这次会议上会有人操事,所以看热闹的人比科学家多一些,先后来了大约七百多人,小会场坐不下了,于是搬到新落成的牛津博物馆继续开会。 当几位科学家读完自己的报告以后,威尔福伯斯主教站了起来,主教长期滔滔不绝地教育信徒,已练成了一副辞藻华丽的好口才,而且他精通数学,也略通地质学和鸟类学,是当时英国科学促进会的副会长。为了维护正统的教义,主教以非常轻蔑的语气谈起了进化论,猛烈攻击达尔文的学说以及达尔文的朋友。 主教发言的详细内容现在已不得而知,据各方考证及当事者回忆,主要观点与他此次会议之前在1860年7月《评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内容相差不大。在这篇很长的文章中,主教列举了达尔文的主要论点,然后指出达尔文所用的演绎方法是不科学的,他还是相信培根的科学方法论:“我们是归纳哲学的忠实学生,不会因任何荒诞的结论而从中退缩。”主教举例说,“牛顿是因为受到苹果下落而发现了天体运行的规律的话,如果达尔文也能采用这种精确的推理方式向我们证明人类与动物的血缘关系,我们将相信他的理论,并自甘与动物界平起平坐,从心里摒弃我们的自豪感。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承认,我们与地上生长的蘑菇也有一定的亲缘关系。” 但是,现在达尔文采用的却是用“异想天开的幻想”来代替“严格的逻辑推理”,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我们坚决反对。 主教还运用自己的生物学知识举例证明物种是不变的,他非常有信心地告诉在座的听众们,野鸽总是野鸽,家鸡不会变成凤凰。达尔文物种进化的理论从根本上是不可理解的,那只是一个以“最大胆的假设为基础的纯粹假说”。
为了更有说服力,主教一一列举了《物种起源》中十处最具猜测性的段落,然后严正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主教告诉大家:“我们对达尔文理论的反对,是在严肃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的。达尔文如果要让我们相信,他的论点就必须接受真伪的检验。” 主教还认为,已有的事实并不能确保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假设。它既违背科学精神又与人类的利益相对立。 令主教大人高兴的是,当时的一些最著名的科学家也站在主教的一边批评达尔文的理论,比如前面提到的开尔文和麦克斯韦等人,还有塞奇威克及达尔文的导师享斯罗。而这次会议正是享斯罗主持的,这让主教大人的腰杆硬了很多。 威尔福伯斯主教采取了一个聪明的策略,他没有借助上帝来打击达尔文,而是试图从科学方法论上踩死进化论,这更符合他作为一个科学协会副会长的身份,也可以给听众造成可以信赖的感觉。此后的神创论者不断拾起他们祖师爷传下的这一秘制绝招,从科学中寻找力量来打击科学,奋力要把达尔文推下圣坛。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进化论被打倒,神创论就可以雄霸天下了。似乎在他们的眼里,根本视佛教和穆斯林等其他众神为无物。 虽然威尔福伯斯的演讲引人入胜,但是他做了一件不该做的蠢事。演讲快结束的时候,他转向了在座的赫胥黎,用挑衅的语气道:“听说赫胥黎教授曾说过,你不在乎一个人的祖先是不是大猩猩。当然,如果这位博学的教授是在说你自己的话,我们便不反对。”接着,威尔福伯斯主教又加了一句:“那个声称人与猴子有血缘关系的人,究竟是他的祖父还是祖母,还是从猴子变过来的呢?” 参加会议的胡克事后回忆说:“赫胥黎勇敢地应战了,那是一场激烈的争论。” 据说赫胥黎在回应以前,先是对身旁的一位朋友说:“感激上帝把他交到了我的手上!”接着就冷静地站起来,大步走向讲台,先从专业角度反驳了主教大人所介绍的肤浅而可怜的生物学知识。赫胥黎坚决反对只把生物进化理论当作一种假设。他指出,达尔文的学说是对事实的解释,《物种起源》中也列举了大量事实,虽然这一理论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已是目前为止对物种问题的最好解释。他不是完美的科学理论,但确实是科学理论。 赫胥黎坚信,达尔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不仅严格地符合科学逻辑的标准,而且也是唯一合理的方法。那就是,通过观察和实验发现大量事实,然后在这些事实基础上进行推理,并得出结论,最后再把结论和自然界中观察到的事实进行比较,以检验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这一辩论正是针对主教对达尔文研究方法的指责而发,有力地回击了主教的批评。 赫胥黎最后语气坚决地总结说:“我声明,我再次声明,一个人,没有理由因为可能有一个大猩猩祖先而感到羞耻。真正应该羞耻的是,他的祖先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利用他的聪明才智在自己的领域去获得成功,而是利用他口若悬河的言辞、偷梁换柱的雄辩和求助于宗教偏见的娴熟技巧来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借以干涉他自己不懂的科学问题。” 因为双方用词激烈,唾沫横飞,台下观众也情绪激昂,会场充满了暴躁的气氛。因为场面过于紧张火爆,一位布劳斯特太太当场被吓晕了过去,她实在想不到这些平日里文质彬彬的科学家和素有修养的主教也会如此地刻薄相向。 当时还有一个人,就是“贝格尔”号船长罗伊也在座。这个性情激动的家伙因为把达尔文带上了船而对上帝怀有深深的忏悔情绪,但又对科学一窍不通,只相信《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折不扣的真理,所以也说不出什么名堂来,只是大步走向讲台,泪雨纷飞地指控《物种起源》给自己带来的深切痛苦,并请在座的各位和他一道将达尔文的理论驱出科学论坛,打倒在地,再唾上一口唾沫。不过听众们并不买他的账,一时间台下嘘声四起,硬是将他轰下了台。罗伊别无他法,只好脸色赤红地高举着《圣经》大喊大叫:“这本书,这本书!”此外再也讲不出什么别的话来。 后来罗伊船长因心情郁闷而自杀身亡,与此次打击不无关系。 此次论战后,达尔文也作出了反应。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达尔文竟然认为赫胥黎对主教的反击“似乎是一次彻底的失败”。是不是因为赫胥黎没能把主教挑出来的那十个疑问给化解掉呢?达尔文在给胡克的信中承认主教的辩论技巧非常老道,是一个聪明的对手。以至于他不得不抽时间把主教指出的那些推测部分一一找出来重新加以审订,以确认不再给对手留下把柄。 纵观整个论战过程,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表象。人们一贯认为这是一场科学与宗教的斗争,似乎这个理解是所偏差的。因为威尔福伯斯虽然是主教身份,但他打出的牌却是科学方法论,他利用的是他另一个身份,也就是英国科学促进会的副会长的身份对达尔文的理论提出挑战的。而赫胥黎也针对性地进行了回击。赫胥黎战胜威尔福伯斯,某种意义上说,貌似是一种科学范式战胜另一种科学范式的口水故事。科学哲学家拉塞尔(Colin Russell)曾就此总结说:“19世纪末在英国发展起来的科学与宗教的敌对关系,与其说是由科学事实对神学和有组织的宗教的威胁引起的,不如说是由新一代知识分子如何认识文化的领导地位问题引起的。”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争夺科学利益和权力的战争。
但在场的胡克的评价却是:“著名的1860年牛津会议,在赫胥黎的生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那不只是一个解剖学家反驳另一个解剖学家,也不是关于事实证据和抽象论断的论战,而是个人之间的才智之战,是科学与教会之间的公开冲突。” 实质也正是如此,“牛津大战”确实是如假包换的科学战胜宗教的里程碑。因为威尔福伯斯主教身披的外衣虽然不同,但他想要打倒达尔文理论的本质目的却正是为了维护上帝的权威和教义的正统。他虽然没有把上帝请出来直接参战,只能说明他的手法是高明的,也是在那种场合下比较合适的方案,因为那毕竟是一场科学大会。 经过这场论战,教会在科学界的影响急剧下降。1865年前三十年间,先后有四十一位教士担任英国科学促进会各五个专业委员会主席;而在1865年后三十多年间,只有区区三人占有了这些位子。 这种影响还在继续,到了1996年,罗马教皇保罗二世(John Paul Ⅱ)致信教廷科学院全体会议,明确表示:“信仰并不反对生物进化论”,“新知识使人们承认,进化论不仅仅是一种假设”。对达尔文来说,这是一个迟到的声明,一百多年后,战争终于在对手那里分出了胜负。 所以,达尔文研究专家摩尔(James Moore)以夸张的笔调称,这是继滑铁卢战役之后十九世纪最著名的战争。 这场论战虽然以进化论大获全胜而告终,而且也在普通读者中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科学是正确的,宗教是保守的,进化论是可以相信的。人们欢呼科学的胜利,希望科学能满足他们更多的好奇心。但此次论战隐约间提出的一个问题却摆在了所有人面前:既然生物是进化而来的,那么人是怎么来的?难道真的也是进化出来的?或者还是上帝情有独钟的手工制造产物? 我们万能的人类,在生物界应该坐第几把交椅呢? 这一次,轮到进化论内部吵成一团了。
赫胥黎:根据解剖学研究,人类与大猩猩和黑猩猩等灵长类动物存在密切关系。换句话说,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 女教徒:我的天啦,这是真的吗? 赫胥黎:根据我们的研究,这确是真的。 女教徒:让我们向上帝祈祷这不是真的。 赫胥黎:很不幸,夫人,我不能骗您,也不能骗自己。 女教徒:上帝!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希望没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 赫胥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