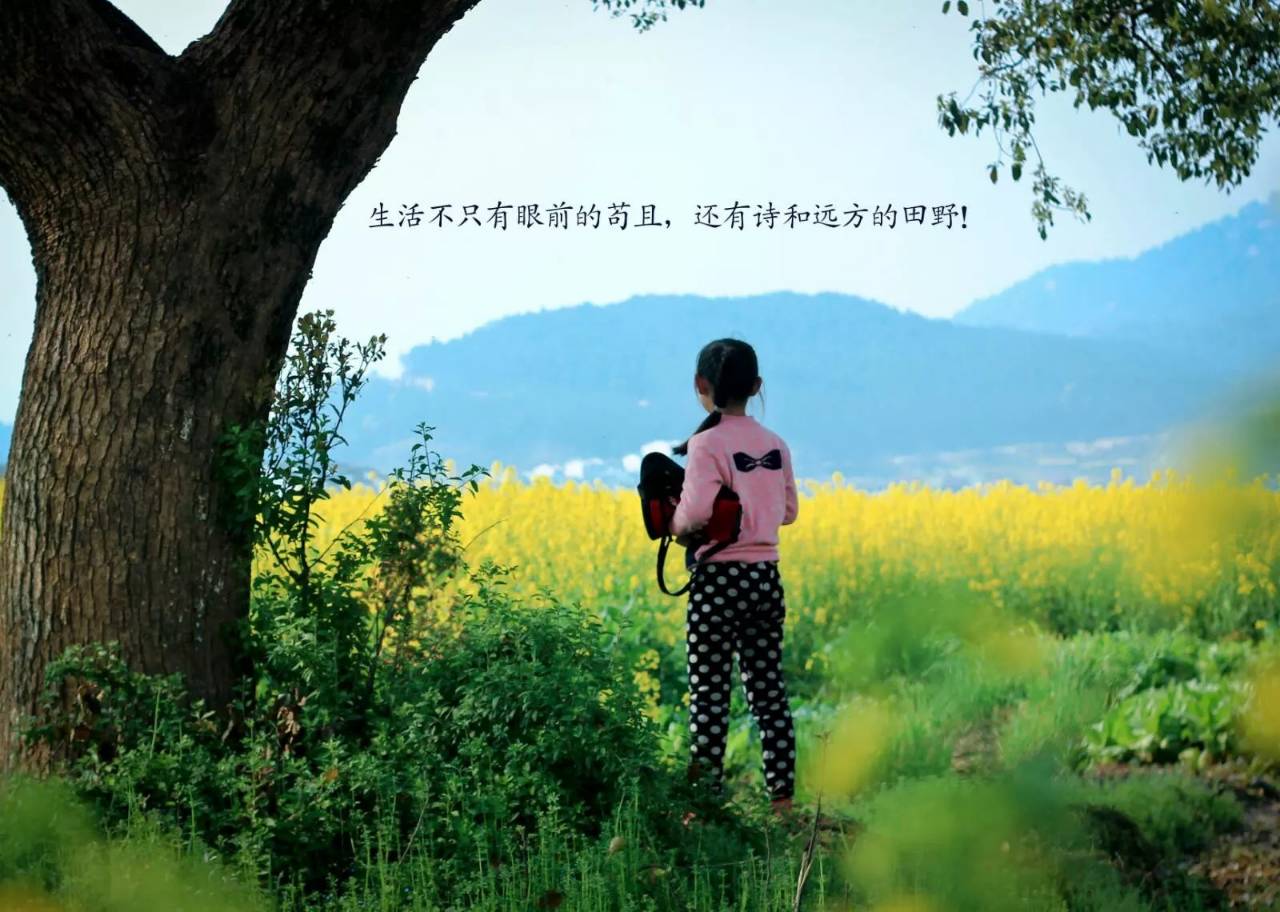| 学术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幸福的组合论是什么 › 学术 |
学术
|
一 幸福基础理论研究 (一)幸福的内涵界定 1.幸福的语义内涵。对幸福内涵的界定是幸福元理论研究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邓先奇认为,在西方语境中,幸福意味着愉快、满意、满足等;在中国语境中,幸福是“幸”与“福”的集合,其中“幸”的涵义包括幸运、幸福、高兴、希望等,而“福”则与“祸”相对,代表着福利、幸福和利益。为此,《现代汉语词典》将“幸福”定义为: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生活、境遇)称心如意。《辞海》则将“幸福”定义为在为理想奋斗过程中以及理想实现时感到满足的状况和体验。 2.幸福的学科解释。王海明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幸福是对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的心理体验和心理反应,是对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快乐。万俊人从伦理学层面将幸福解释为:幸福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人们对生活经验的主观感受,当然也是一种生活价值的评价;相对于每个生活的个体来说,幸福是真切的,当你感到了一种舒适感、一种成就感、一种特别的快乐、一种称心如意的感觉,那就是幸福。 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从哲学命题上提出:“幸福是完善的和自足的,是所有活动的目的。”近代哲学家冯友兰则把幸福看做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认为“独立自足的生活,即是合理的幸福”。《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将幸福界定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因目标和理想的实现或接近而感受到的一种内心满足”。从对幸福的哲学解释中可以概括出:幸福是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使人的主观需要与外在客观条件相互满足的精神和物质状态。
通俗地说,幸福是一种生活化了的实践感受,是精神感受与物质具象的有机统一。比如:有的人将幸福概括为“六个好”,即人人有个好工作、家家有个好住所、处处有个好环境、时时有个好心情、年年有个好收成、一生有个好身体;有的人则将幸福归纳为“八个一点”,即岗位更多一点、学费更低一点、看病更省一点、住房更舒适一点、物价更稳一点、空气更净一点、事故更少一点、治安更好一点。 (二)幸福的本质与要素 1.幸福的本质属性。韩敏等人认为,对幸福的科学认识,需要辩证地看待幸福的本质属性或辩证关系;幸福的本质属性寓于人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相对性与绝对性、个体性与群体性之中,是人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相对性与绝对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的有机统一,体现出一定的辩证性。章建明、巢传宣则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属性出发,将幸福的本质归结为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实践活动,包括外在的个体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和内在的个体需要得到满足时的主观心理体验。 王艺认为幸福的本质属性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并具有道德性、和谐性、共享性、精神性、超然性、适度性、简单性和价值性等本质特征。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幸福的本质属性既有主观性,亦有客观性,而其根本属性则在于社会实践性,即幸福离不开人的社会实践,而人的幸福正是在人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得来的。 2.幸福的结构要素。早在古希腊时期,思想家柏拉图就认为幸福由“蜜泉”和“清凉剂”两个要素构成,分别代表着感性生活和理性生活,而且单独的感性生活和理性生活都不能获得幸福,“只有利用我们自身的力量,使这两股清泉合理配置,才能够成为理想的合剂———幸福”。 这是典型的二要素论。英国心理学家卡尔和皮特则是三要素论的代表,他们认为真正的幸福包括生存、个性和高层次的需要三个要素,且三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关系,可用公式表示为:幸福=P+5E+3H。其中,P代表个性判断,E代表生存状况(5E包括身心健康、收入状况、安全感、自由度、客观条件),H代表高层次需要(3H包括自我评价、期望水平、抱负和幽默感)。 四要素论者则认为,幸福由金钱、情感、自由和信仰四个要素构成,幸福的要义并不完全由金钱等物质条件所决定,还受情感、自由和信仰等精神要素的影响。可见,幸福的构成要素是多元的,既包括感性生活和理性生活,也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从其结构类型来看,则可以概括为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两大类。 (三)幸福的元理论学说 1.中国传统幸福论。中国传统幸福论主要以儒家幸福观、道家幸福观和中国化了的佛家幸福观为代表。儒家虽然追求“内圣外王”,但很少使用“福”字,而是用“乐”字代替“福”字,以表达人的主体自我感受,更加注重精神上的幸福感受,追求中庸和谐的幸福人生。
道家主张清静无为,顺其自然,过原始质朴和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其对幸福的看法主要见诸于“天福”观念,认为人生的一切皆由“天命”决定,因而实现人生幸福的途径在于顺应自然、“安时而处顺”。佛家有苦、集、灭、道四圣谛,认为人生本无幸福可言,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痛苦,只有摆脱痛苦的“生死轮回”,才能达到幸福的彼岸——“涅磐”境界。可见,中国传统儒家、道家、佛家尽管宗旨不同,但在幸福理念的追求上颇为相似,即更加注重人的精神幸福,而不是物质生活。 2.西方传统幸福论。西方传统幸福论主要表现为感性主义幸福观、理性主义幸福观和基督教神学幸福观三大传统。其中,感性主义幸福观强调幸福的主要源泉是感性而不是理性,认为人的幸福主要在于人的感性欲望的满足与快乐。其代表观点包括阿里斯提卜的肉体享乐主义、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爱尔维修的“利己与利人”主义以及边沁的功利主义等。 理性主义幸福观认为人生的目的和幸福在于按理性命令行事,主张抑制欲望,贬低感性与情感的作用,而追求道德的完善或精神上的幸福。其代表性观点包括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和谐说和以犬儒学派和斯葛特学派为代表的禁欲主义。基督教神学幸福观则认为幸福不在于对财富、名誉、权力和肉欲的享受,而在于对上帝的热爱和追求中;尘世生活不过是趋向上帝天国的旅途,德行是达到幸福的手段,只有保持对上帝的沉思、崇拜才能返归天国,最终获得真正的幸福。 3.马克思主义幸福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幸福是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只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才是人生的最大幸福。其中,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论的理论基础,集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论的核心,而实践活动则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根本途径。 总之,马克思主义幸福论体现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享受与劳动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幸福的统一。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幸福论兼顾到了幸福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不是把幸福归结为禁欲主义和享乐主义,而是根据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强调幸福的社会实践性,是社会生活条件在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中的反映,人们才把马克思主义幸福论视为科学合理的幸福哲学。 二 幸福专题理论研究 (一)幸福感、幸福观、幸福指数 1.幸福感。幸福感是个体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因而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苗元江认为,幸福感是“主体与现实生活情境的协调及自我达到完满统一的自我认同及自我欣赏的感觉,并由此而产生的积极性情感占优势的心理状态”。邓先奇认为,幸福感不仅仅指个体生活追求、潜能展现、价值实现而获得的满足感,还指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关系融洽而获得的认同感、和谐感等。 因此,他把幸福感的外延拓展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谷安霞认为,幸福感受各种外因和内因的影响,其中,外因包括经济状况、文化差异和社会关系,而内因主要包括人格特质、健康状况、教育与认知等。康君则提出了衡量国民幸福感的8项指标,即富裕感、愉悦感、期望感、安定感、归属感、向心感、自由感、情谊感。Dierner将西方幸福感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描述比较阶段,侧重于从人口统计学维度对不同群体的幸福感进行比较和描述;二是理论建构阶段,重在研究幸福感形成的心理机制,并根据认知理论、目标理论、适应理论、人格理论等建构相应的理论模型;三是测量发展,完善和发展幸福感测量技术,建构幸福感测量指标。
谷安霞也将国内学者对幸福感的研究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属于引述阶段,重在介绍国外研究理论;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期)属于应用阶段,开始结合中国实际,运用国外理论和研究工具进行实证研究;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则属于飞速发展阶段,不仅开始出现多元化发展,而且注重本土化和跨文化的研究与建构。由于幸福感具有主观差异性,因而体现出了不同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2.幸福观。幸福观属于哲学范畴,因而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李琳认为,幸福观是人们关于幸福目标、幸福手段、幸福标准、幸福期望等问题所持观念的总和。王美华认为,幸福观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延伸与发展;幸福观深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幸福观也就各不相同。姜丽华把中外幸福观概括为快乐主义幸福观、完善论幸福观和合理幸福观,并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才是科学合理的幸福观。 王美华则分别对古代西方幸福观、近代西方幸福观、现代西方幸福观、后现代西方幸福观,中国儒家幸福观、道家幸福观以及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毛泽东时代的幸福观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幸福观进行了分析和总结。陈永在比较分析中西方幸福观差异的基础上指出,西方幸福观总体以崇利、逐利为代表,在价值取向上,中国讲仁义,西方看重的是实利;中国幸福观始终是儒家的道义论幸福观占主导地位,且个体幸福始终寓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幸福之中,而西方则从只关心个人幸福过渡到注重兼顾大多数人的幸福。 3.幸福指数。最早提出幸福指数概念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将人们的幸福用一个方程式来衡量,即“幸福=效用/欲望”,假定欲望是既定的,消费的物品越多,所得的效用越大,人们就越幸福。在我国,钟永豪、林洪、主要侧重于任晓阳等人最早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NHI)的概念,认为国民幸福指数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据此设计了衡量国民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包括物质生活指标体系和精神指标体系两大部分。 其中,物质生活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恩格尔系数、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主要耐用消费品年占有量、人均年末住房面积、个人及家庭的社会保障状况、人均主要农畜产品消耗量、每万人的卫生健康状况等,而精神指标体系则主要包括个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教育就业状况、人际关系状况、婚姻家庭状况、精神享受状况以及个人对环境的满意程度、权利保护与实现状况等。周四军等人则根据已有的国民幸福指数研究成果,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与就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四个方面,选取了25个指标,重新构建了国民幸福指数的指标评价体系。 (二)国民幸福、民生幸福、幸福悖论 1.国民幸福。陈艳丽把国民幸福界定为国民幸福感,即国民实现自身人生理想和预定目标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李彩霞则认为,国民幸福是由主观与客观元素糅合而成的“重大需要、欲望、目的等正面因素得到实现,负面因素得以避免的心理体验;也是生存发展达到某种圆满,物质追求获得某些满足的客观体验”。 而对国民幸福的量化与实践研究则是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其中,宏观层面的研究以“不丹模式”为代表。“不丹模式”是指强调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的均衡发展,认为资源环境的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促进优先于经济发展,主张用国民幸福总值(GNH)代替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发展标准的独特模式。
不丹政府将国民幸福总值具体化为持续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文化传承和政府善治四大支柱。我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等人则根据中国实际提出了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大要素构成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中观层面的研究主要以中介机构、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为代表。例如:2005年,美国《福布斯》杂志用“税负痛苦指数”来衡量公司员工的幸福指数;2006年,北京市统计局首次将国民幸福指数纳入和谐社会评价体系;2011年,广东省则着力从主观与客观两套指标体系来建设“幸福广东”。 另外,刘扬、邹伟、王小梅等人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最新的理论成果——国民时间核算(NTA)方法,用U型指数来测量北京市民的幸福水平。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个体、单位、行业以及特定群体的幸福感测量。譬如,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用个体的幸福体验来衡量国民的幸福指数,提出生活质量是衡量幸福指数的核心。我国的邢占军,张静平、叶曼、朱诗林和姚晓宁、黄红云、张玉、熊赵等人则分别研究了城镇居民、贫困地区老年人和公务员群体的幸福感指数。 2.民生幸福。李跃华认为,民生幸福是社会发展的伦理向度,它以“美好生活”为本位,以国民幸福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以民生改善为政策取舍的依据和衡量发展得失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败的标尺。 夏颖认为,民生幸福的本质在于:物质利益是实现民生幸福的基础,分配正义是实现民生幸福的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民生幸福发展的终极目标;其测量标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理论测量指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践测量指标——群众满意度;而实现民生幸福的责任主体是政府,主要实现路径在于构建以人为本的幸福观。 王忠武和许静认为:生存、生活、生计既是民生问题的基本层次,也是民生幸福的基本来源与构成维度;生命生存、生活条件和生计工作对民生幸福具有重要的影响;促进和实现民生幸福,需要创建以民生幸福为目标导向的新型社会管理体系,致力于实现民生资源的最大化供给和最优化配置,促使各种民生问题的良好解决和民生利益的良好实现;其基点是优先改善民生,基本目标任务是通过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和提升公共服务来有效保障民生需要、改善民生条件,最终实现社会和谐与民生幸福。 而赵嫦娥、罗建文等人则认为,加强制度建设才是实现民生幸福的根本保障,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分配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监督机制、长效机制的建设等,使改善民生的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 3.幸福悖论。幸福悖论亦称伊斯特林悖论、“收入—幸福之谜”等,由美国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于1974年在《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首次提出。幸福悖论主要是指人们的幸福感与物质财富增长之间的不一致现象,它证明了收入与幸福之间普遍存在的弱相关性。 针对这一现象,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和研究。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相关理论解释共有8种,即边际幸福递减理论,攀比效应,棘轮效应,非物质因素影响理论,幸福度定点理论,“享乐水车”效应,“满意水车”效应,“社会水车”效应。 这些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忽视变量理论和比较视角理论两类。忽视变量理论认为,经济学仅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而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许多重要因素,如激励与创造、健康、政治参与、社会渴望、自由、利他主义的丧失、不平等、社会资本的减少和地位外部性等;比较视角理论则从收入本身出发,认为个人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 针对幸福悖论现象,不同的研究者也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比如:程实认为,克服幸福悖论的方法之一就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田国强和杨立岩提出通过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包括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基本人权、防失业与通货膨胀等)的方式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陈惠雄、邹敬卓认为,化解幸福悖论,必须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对生命和生活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黄有光则认为消解幸福悖论的前提是政策制定者要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为诉求,只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时,幸福悖论才不会充斥于世界的各个角落。 (三)幸福问题、幸福归因、幸福路径 1.幸福问题。在幸福问题的研究方面,国外学者更多地是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背景进行分析和研究;而国内学者则更倾向于结合中国实际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宏观层面进行研究。
比如,马红坤认为,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幸福问题是收入差距拉大、工作压力加大、“空巢”问题日益严峻、社会公平感欠缺。周怡也认为,目前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提升的主要障碍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民众就业压力持续上升,教育、医疗、住房问题成为老百姓新的“三座大山”,就业压力持续上升,社会保障相对滞后,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精神幸福感欠缺等。王志立则从资源困境、社会困境和心理困境三个方面指出,“风景不在”的生态环境影响对幸福的主观感受,“变动不居”的社会环境影响对幸福的亲身体会,“感情淡疏”的人际环境影响对幸福的心理体验。 王艺却认为,当前人们追求幸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有限的资源大量用于追求那些低层次的、仅仅蕴含有限价值的幸福类型,而忽略甚至牺牲了那些更高层次的、蕴含着更丰富价值的幸福类型,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是过分追求物质幸福而忽视精神幸福,过分关注结果幸福而忽略过程幸福,并由此造成了现实世界中消费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的泛滥和一系列的生态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经济危机、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等。 2.幸福归因。在幸福问题的归因方面,国外学者多数从收入、年龄、婚姻状况等微观层面对幸福问题进行因素分析和实证研究,以便从中找寻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有部分学者还将影响个人幸福的因素扩展到性别、失业、社会公平、文化教育、生态环境、气候条件等方面,并进行综合分析。 而国内学者则更倾向于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进行问题归因。例如,马红坤从价值层面认为,幸福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化浪潮对幸福感的冲击和多元价值观对幸福价值观的冲击,包括金钱至上主义价值观、消费主义价值观、功利主义价值观等。韩敏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问题归因,认为信仰、价值观、文化传统、文化环境等文化因素对人们的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 其中:信仰是影响人们生活幸福的最高精神因素,有没有信仰或信仰什么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进而直接影响人们对生活的评价和感受;而价值观则制约着人生目的、人生道路以及人生幸福观;不同的文化传统铸造不同类型的民族性格,而不同性格倾向的人对生活状态的营造及满足感各不相同;文化环境对民众自身生活状态的评价和满足感只具有相对意义,因而国民幸福感不一定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增强。 邓先奇则认为导致幸福问题的根源在于异化劳动,即异化劳动使人无法依据自己的本质来追求幸福,把人的类生活变成了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将人等同于动物,使人们沉迷于物质消费而失去自我;正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面对立,阻碍了人类幸福的实现。 3.幸福路径。关于幸福实现的具体路径方面,中外学者均注重从物质条件、社会制度、个体因素等方面进行探究。相对而言,国外学者更加注重精神路径和微观层面的探讨,国内学者则更加注重宏观层面的综合路径探索。
比如,王旭丽认为,实现国民幸福的主要路径在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提高精神生活水平;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实现和保障人的尊严;加强人文关怀,促进人的心理和谐。王志立针对资源困境、社会困境和心理困境问题提出了实现幸福的三条路径:实现人同自然的和谐——提升国民对幸福的主观感受;实现人同社会的和解——提升国民对幸福的亲临体会;实现人与人的和睦——提升国民对幸福的心理体验。 谷安霞认为,提升国民幸福感的路径在于外在条件的满足和自身因素的具备,其中外在条件包括调节和引导经济持续发展,加强环境保护,调节社会贫富差距,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内在因素包括知识、道德、创造、享受、奉献等。 周怡认为,提升民众幸福感的具体措施在于:政府应确立以国民幸福为核心的社会发展体系,包括解决老百姓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加强对国民现代意识与健全人格的培养和塑造;转变生活理念,以追求快乐幸福为终极目的和终极价值;引导全社会更多关注弱视群体主观幸福感,把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其政策全面调整到以多数人幸福为核心的层面上来;建立社会公平与公正体系,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等。 三 幸福研究基本评价 (一)幸福研究的基本特点 1.现实性。幸福研究的现实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幸福问题一直是中外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话题。从西方的《幸福之路》(罗素,1930)、《幸福散论》(阿兰,1925)、《幸福的终结》(弗格森,1992),到中国的《幸福论》(陈根法、吴仁杰,1988)、《西方幸福论》(冯俊科,1992)、《人生幸福论》(陈瑛,1996)、《幸福论》(高兆明,2001)、《幸福论》(孙英,2004)、《幸福学概论》(丁心镜,2010)、《幸福奥义》(饶贵民,2013)、《中国幸福之路》(韩跃红,2013)等等,都对人们思考幸福问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幸福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比如,西方学者对“幸福陷阱”和“不丹模式”引发的国民幸福指数研究,以及中国学者针对现实生活中的幸福障碍和中国社会发展中各种有悖幸福生活的“社会病”的研究等,均引发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反思和启迪。第三,如何实现人们的幸福追求,这也是中外学者着力研究解决的现实课题。对此,西方学者已从微观层面给出了许多具体的答案,而中国学者更多地从宏观层面提出了系统的实现路径。 2.多元性。幸福研究的多元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幸福内容与范畴的研究具有多面性,既有对幸福的内涵、本质、特征、学说等基础理论的研究,亦有对幸福感、幸福观、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民生幸福、幸福陷阱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同时还有对幸福与人生、幸福与发展、幸福与社会、幸福与健康、幸福与环境等多领域的辩证研究。 其次,幸福研究的方法论具有多样性。比如,中外学者在研究幸福问题时,均注重从哲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运用跨学科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对幸福学研究方法的开拓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再次,在研究视角方面,既有宏观研究,亦有中观和微观研究,同时也有综合性研究等,这也体现了幸福研究的多元性特点。 3.实证性。幸福研究的实证性是幸福问题研究方法运用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主要反映在针对幸福感及国民幸福的测量研究和指标体系建构方面。比如,针对幸福陷阱的实证研究就有“边际幸福递减”模型,“囚徒困境”模型,线性概率模型,“幸福=收入/欲望”模型,代表性消费者模型,相对收入理论模型,幸福度的基本理论测度模型等等。 我国对幸福问题的实证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实践应用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钟永豪、林洪、任晓阳的《国民幸福指标体系设计》(2001),邢占军的《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2005),李桢业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省际差异———沿海地区12省(区、市)城市居民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2008),苗元江的《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幸福感理论与测评研究》(2009)等。 (二)幸福研究的不足之处 1.对幸福因素的作用机理尚需深入探讨。幸福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幸福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影响幸福的各种因素可以概括为内在因素(包括认知水平、道德修养、个性特征、身心状况等主观条件)和外在因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客观条件)。 这些影响因素均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和作用机理,而目前针对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和制约幸福发展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尤其是各种影响和制约因素的内在机理如何发生作用以及对其作用的效果如何评估与检验等,尚需做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2.对幸福的差异性研究尚需充分把握。幸福既有国际性,亦有国别性。就我国的幸福发展而言,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客观条件的差异性决定了中国幸福发展的现实差异性,而幸福主体——国民的个体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性不仅决定了衡量国民幸福指数的差异性,而且也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与人民幸福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是当前促进我国社会发展与提升国民幸福指数必须充分把握的特殊国情。 3.对幸福的探索研究尚需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幸福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实践应用,在于解决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幸福问题。目前,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快速发展进程中,不仅面临经济发展与幸福发展不一致的“幸福陷阱”问题,而且还面临许多影响人民幸福感和国民幸福指数的各种“社会病”。针对这些现实问题,尽管中外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但依然收效甚微。具有中国特色的幸福学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幸福研究的发展趋势 1.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中国的幸福学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不过幸福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这也为幸福学理论研究留下了创新发展的空间。借鉴国外成熟的幸福学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建立中国特色的幸福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中国化、本土化、特色化的幸福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幸福学研究理论创新的发展方向和根本任务。
2.方法运用的探索突破。国外幸福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引入中国后,逐步开拓了中国幸福学研究的方法视域。但是,相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幸福问题的不断涌现,中国幸福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突破还比较滞后。多学科的综合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具体应用以及新方法的创新,既需要在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幸福问题中发展完善,更需要在实践运用和探索研究中取得新突破。这也是未来中国幸福学方法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3.实践研究的深化发展。中国的社会发展永不停歇,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永无止境,由此决定了对中国社会发展与人民幸福的探索研究尚需继续深化发展,尤其是结合中国实际,运用国内外幸福研究理论指导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幸福问题。 实践既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亦是促进探索研究的动力源泉。新的实践促进新的探索,新的探索激发新的创新,新的创新推动新的发展。中国社会的新发展以及人民对幸福追求的新要求决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幸福学研究将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对中国幸福学研究提出的一项实践任务。 本文摘自2014年《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14卷,图片来自石清泉摄影 更多精彩分享敬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总编辑:韦志中 责任编辑:孙艳 陈领芬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