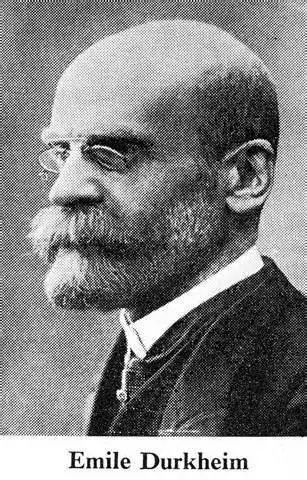| No.634 赫伯特·哈特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conscience的意思 › No.634 赫伯特·哈特 |
No.634 赫伯特·哈特
|
译者简介
马腾,广东汕头人,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关于法律对道德强制执行作用的以下论点,即城邦法之存在不仅是为了保障人民有机会过上有德性的美好生活,还在于要求他们如此生活,可以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也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中提炼出来。根据这一论点,法律不但可以用于惩罚那些犯下道德错误的人,而且应当这么运用;通过这些(以及其它)手段用于促进美德,这是一个足够复杂的社会发展出一套法律体系的宗旨或目的之一。这一理论与某种特定的道德观紧密联系,作为一种唯一真实或正确的原则集合,这种道德观并非人造,而是要么留待世人运用自身理性去发现,要么(在神学背景下)等候天启揭示。我将这一理论称为“经典命题”(the classical thesis),且不做进一步论述。 我所称的“瓦解命题”(the disintegration thesis)与经典命题有所区别,它倒置了出现在经典命题中的社会与道德之间的手段顺序。因为在这种论点中,社会不是道德生活的手段,反而是道德因其作为巩固社会的基石,以及维系社会的纽带或者众多纽带之一而具有价值。缺乏这些纽带,人们将无法凝聚于社会中。这一论点与某种相对主义道德观紧密联系:根据这种道德观,道德在不同社会之间各有不同,而且值得以刑法强制执行的道德,无需拥有理性或其它特定的内容。这与道德品质无关,而是凝聚力的问题。“重要的不在于信条的品质,而在于其中信念的强度。社会的敌人并非错误,而是冷漠。”[i]由此观之,我们保持道德法律强制的理由之一,就是它对于防止社会瓦解之必要性。 需要经验性证据以证实维持道德在事实上是社会存续之必要,在这种压力下瓦解命题往往沦为我所谓的“保守命题”(the conservative thesis)。这一命题主张,社会有权通过法律强制执行其道德,因为多数人有权秉持这一道德信念,即道德环境是一种具有价值而应保卫免遭改变的东西。[ii] 本文要讨论的对象是瓦解命题,为了完成这一论证,我将自己在本文的论证任务限定在那些与这个命题有关的数量极为有限的一组任务上。我主要做的是:在祛除模糊之后,尝试揭示这一命题做出的经验性主张是什么,以及在什么可能的方向上,搜寻支持这一主张的证据是有意义的。但即便如此,我也仅仅部分讨论这些论述内容。 一 瓦解命题是德富林关于道德的法律强制论证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在此,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信徒以及其它后来的自由主义者会认为,这是一种对刑法范围的不合理延伸。按照德富林勋爵的说法,在证成道德的法律强制时,道德被描述成各种社会的“道德结构”(the moral structure):“一种公共道德”、“一种共同道德”、“关于政治、道德、伦理的共享观点”、“关于善恶的基本共识”、“公认道德”。[iii]这被称作是维系社会的“看不见的共同思想纽带”;而“如果这种结合太过于松散,社会成员就会相互疏离”。[iv]这既是“社会束缚”的一部分,又是“对社会和一个获得民众承认的政府来说必不可少的”。[v]强制执行承认道德的证成仅仅是,法律可以用于保护任何对社会存在必不可少的东西。“当公共道德不被遵守,社会就会瓦解。历史表明,道德纽带的松弛往往是社会瓦解的第一步”。[vi]如果我们考虑这些构想,它们似乎构成一番有关社会存在之必要条件的极具抱负的经验性归纳,从而给我们呈现了社会瓦解的充分条件。除了“历史表明,道德纽带的松弛往往是社会瓦解的第一步”这个一般陈述,这里并没有给出证据支持论证,没有指明能够支持的证据类型,也没有对证据的必要性表现出丝毫敏感。 在与德富林勋爵论辩的过程中,我为他提供了二选一方案,要么以证据补强论证,要么承认他关于共同道德对社会存在的必要性根本不是一种经验化陈述而是同义反复的伪装,抑或这种必要性的真实完全取决于如何定义“社会”、“存在”或“存续”。如果社会存续的意思是根据一些特定的共同道德法典生活,那么保存一部道德法典只是在逻辑意义上对社会的存续必不可少,而非因果意义或或然意义上的必要性,从而似乎就是一个过于乏味的主题,不值得公开讨论。不过在这一点上,德富林勋爵所采取一个社会定义(“一个社会意指一个观念共同体(a community of ideas)”[vii]),似乎表明他关于道德对社会存在必要性的陈述是一种定义的真实(definitional truth)。当然,“社会”、“社会存在”以及“同一社会”的表述很常以这种方式使用:即它们指向一种社会生活的形式或类型,而将一种社会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区分开的标准就在于某种特定道德,或道德法典,或独特的法律、政治、经济制度。若我们将社会理解为具有某种形式或类型的社会生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是可以改变、消亡的,或是可以被不同的社会形式所接替,而不具有任何可以描述为“瓦解”或“成员相互疏离”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的“社会”,后封建时代的英国就是一个不同于封建时代英国的社会。但如果我们将这个简单的事实换成这样的表述,说同一个英国社会,在一个时代是封建社会,而在另外一个时代则不是,那么我们就使用了另一个意义上的社会概念,也就是换了一套不同的标准来区分各种社会或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延续。显然,如果社会瓦解或“成员相互疏离”的威胁具有任何真实情况,或者如果共同道德“对社会和一个承认的政府来说必不可少”这一主张被作为强制执行道德论证的一部分,那种以共享道德作为识别某个社会的标准的做法,只能推出一种定义上的真实,与这个论证毫无关联。正像如果通过“有组织的社会”一词,我们只将社会理解为一个有政府的社会,那么“政府对于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来说是必要的”的说法,就不会从那些想要保存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得到回应。同理,如果原来是要以社会一词意指按照这种道德法典生活的社会,那么对一个认为维护社会道德法典并非法律事务的人表示反对,声称维护道德法典对社会存在必不可少,这也是徒劳的。
简言之,如果我们通过“社会不复存在”意指的不是“瓦解”,也不是其成员们的“疏离”,而是社会共同道德的根本变化,那么运用法律维系道德就不能基于瓦解命题,而是基于该主张的某些变式,即当一群人已经发展出一种足够充裕以涵括一种共同道德的共同生活形式,这就是应当保护的东西。该主张很明显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保守命题,即在这些情况下,大多数人有一种保护其既存道德环境免于变化的权利。而这就不再是一种经验化的主张了。 二 与德富林勋爵观点并无二致,且在一些情况下以类似方式游移于瓦解命题与保守命题之间的一些观点,可在很多有关社会结构上与功能上先决条件的当代社会学理论中发现。例如,确实有必要对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的研究进行完整的评鉴,这样可以从中获取那些明显就是关于瓦解命题的构想,这些构想可以从他《社会系统》(The Social System)书中的每一章找到,并进而探究:(i)它们在精确意义上指什么;(ii)它们是否作为经验性主张提出;(iii)若如此,它们可以通过什么证据获得支持。例如,考虑如下这种构想:“对这种共同价值模式的共享……在彼此朝向共同价值的人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团结……没有对基本的共同价值的依附,集体就趋于瓦解。”[viii]“这种对一系列共同价值模式与构成性人格内在化的需求结构之间的结合,是社会系统动力学的核心现象。任何社会系统的稳固都取决于这种整合的程度,这可以称为社会学最基本的动力学定律。”[ix]确定这些命题在帕森斯复杂的研究中的精确意义及作用将是一个颇为宏大的任务,所以我将从社会学著作中选择涂尔干的作品,特别是考察他对特定形式的瓦解命题的深入思考。因为正如在《社会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一书中已详细解释,他对自己多变的理论表述得相对言简意赅,且与通过刑法强制执行道德的主题有专门联系。 对于所谓“团结”(solidarity),或所谓趋于联合人们、致使他们在可辨识而持久的社会中结合的因素,涂尔干区分了两种形式。这里,最低限度意义上的社会是指这么一个群体,我们可以将该群体与其它类似群体区别开来,也可以承认该群体自始至终存在一段时间,即使其组成成员已经在这个时段中被另一些人所取代。团结的其中一种形式,即“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源于人类同一性,而另一种形式“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则源于人类的差异性。机械团结取决于,或可能确实存在于人们有关实际问题的共同信念的共享,以及内在具有某一共同道德的共同行为标准的共享。这种共同信念与共同标准的混合构成了“集体良知”(conscience collective),这利用了法语词汇“良知”(conscience)的所有模糊含义而游移于意识(consciousness)或知识(knowledge)与良心(conscience)之间。使用“良知”这一专门术语的关键主要在于,对共同标准的信念与恪持成为内化于社会成员们人格或性格的一部分。 相反,有机团结基于人类的差异性,基于人们共同需求通过与有异的他人之间多样形式的联合得以补足。这种差异间相互依赖的最突出方面就是社会分工,但涂尔干告诫我们,我们不能将社会分工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联结社会因素所发挥的重要性归结于其经济结果。“相比社会分工产生的道德结果,它提供的经济服务不足挂齿,而其真正功能是在二人或更多人之间创造一种团结的感觉。”[x]概言之,机械团结是简单社会中的一种支配形式,而且重要性日渐式微,尽管表面上它作为一种联合因素从未完全消除,而有机团结则在更为复杂的社会中得以发展。根据涂尔干的理论,法律均可呈现为两种团结形式的忠实写照,且可以用以成为在任何时候评估两种形式相对重要性的一个尺度。刑法以其镇压性的制裁反映了机械团结;民法则反映了有机团结,因为它维持着人们相互依赖的典型工具,如合同制度,所以一般所提供的手段不是为镇压性的制裁,而是为了恢复原状与赔偿。 涂尔干略带幻想地认为,法律可以用来作为一种测量仪器。我们只要在任何时候统计构成刑法的规则数量,统计构成表达社会分工之民法的规则数量,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要打多少分以确定两种形式团结的相对重要性。[xi]这种幻想引致一个难以应付的问题,涉及法律规则的特性与可量化性,这一难题耗费了边沁大量的论述工作[xii],但或许不必在此阻滞我们。然而,真正有重要意义的是,涂尔干对与共享道德有关的刑法具有什么作用的观点。涂尔干很注重展现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关于刑罚制度描述的空洞性。对他来说,正如对英国法庭上的某些与之类似的人物来说,功利主义作为一种解释性理论失败了,因为它扭曲了犯罪与惩罚的特征,且认为作为一种标准理论会导致令人不安的结果。因而涂尔干为犯罪与惩罚提供了别出心裁的定义。对他来说,犯罪就是一种本质上(虽然在发达社会中,存在第二性意义的犯罪,使得这一定义无法直接应用)违反集体良知(保持人们在一起的共同道德,在这一点上其意见既强烈又清晰)的行为。这样一种行为,不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犯罪或错误才被道德谴责,而是因为如此被道德谴责才成为一种犯罪或错误。最重要的是,一种行为错误或构成犯罪无需是,甚至无需被认为是对任何人或社会在任何意义上有害,而是因为在意见鲜明强烈之处,这种行为与共同道德背道而驰。涂尔干理论的这些特征显然与德富林的理论极为相似,德富林注意到这并非道德品质的问题,而是其中信念强度以及随之产生的凝聚力,从而他规定道德必须在所谓群情激昂时强制执行,即必须以“无法容忍、愤怒、厌恶”[xiii]为标志。 那么,按照这一观点,什么是惩罚?为什么要惩罚?以及要多么严厉地惩罚?在涂尔干看来,惩罚本质上因违反共同体道德激发的斗争,这种共同体道德可能普及于整个社会中,或者由官方行动执行而往往具有特定形式的层次分明的标准。因此,他对惩罚的定义是,针对违反集体良知犯罪的“一种具有一定情感强烈程度的激烈反应”。[xiv]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发现,即便在现代社会刑罚也是有等级层次的,那么作为刑罚的一种解释,功利主义理论的空洞性很明显。刑罚并非依功利主义目的适用去预防一般描述的有害行为,而是对犯罪所激起的感觉程度的适当表达,且基于这种适当的感觉表达作为维持集体道德信念的一种方法。[xv]很多法律现象证实了这一点。即便一名抢劫犯很可能再犯,我们对他的惩罚仍轻于一名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不会再犯的谋杀犯。他会补充说,我们在刑事问题采纳了对法律无知不是理由这一原则,我们对未遂的惩罚轻于既遂,从而体现了相比未完成的犯罪,已经完成的犯罪给我们带来的愤恨程度的不同。 因此,涂尔干对“为什么惩罚”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我们这么做,根本上是作为一种引发共同道德义愤的符号表达,对这种共同道德的维系构成因人类相似性之社会凝聚的先决条件。需要通过惩罚罪犯维系社会凝聚,因为对于犯罪所违背的共同良知而言,“如果没有一种社会的情绪化反应(表现为惩罚)来补偿损失,必然地会失去活力,而这会导致社会团结的崩溃。”[xvi] 这番对涂尔干理论的概述呈现出其理论基础,而正如德富林勋爵理论的情形,其中存在两种很重要的复杂性。二者都不免要处理共同道德发生变迁的可能性。两位理论家似乎都想象出一种自发的或自然的转变,并以各自方式告诫我们,职是之故,我们必须允许道德的法律强制。于是德富林勋爵对立法者提出谨慎的警告,即“容忍限度会发生变迁”[xvii],我们不应出于那些不久就会改变的道德观点规定刑事犯罪问题,从而使得法律高不可攀且道德干瘪。涂尔干类似地提到,他的理论并非意味着,因为某种刑事规则曾符合集体情感就必须加以保存,而是只有这种情感仍然“鲜活而充沛”。如果它已经消失或式微,没有什么比试图人为地通过法律保持其存活更糟糕的了。[xviii]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进行区分以下两种变化:一种是社会道德自然或良性的变化或“容忍限度变迁”的正常现象,另一种是社会道德恶性形式的变化,即反对社会受到保护并最终导致个人背离社会道德的结果。然而,在这些理论中还有更为复杂的东西,那就是惩罚的功能,抑或保护一个社会道德免于恶性变化的惩罚执行所运用的机制,涂尔干和德富林勋爵观点有别。对德富林勋爵而言,通过镇压或减少那些本身被认为“将威胁”或弱化共同道德的不道德行为数量,惩罚就保护了既存道德。而对涂尔干来说,惩罚维持了共同道德,主要不是通过镇压不道德行为,而是通过在义愤意义上给予一种满足的宣泄,因为,如果这种宣泄被阻塞,共同的良知将“失去活力”,联合的道德将会式微。
三 对于诸如德富林勋爵与涂尔干的理论,如果我们严格地追问,关于维系共同道德与社会存在的联系,他们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经验性主张,就还需要更深入地理顺这一难题。 对这些理论似乎存在一个很自然的异议,即如果将这些观点真正视为瓦解命题的变式,那么他们试图给出的强制执行社会道德的正当理由就太笼统了。毫无疑问,在社会道德法典(假如真有一部独一无二的道德法典)的各部分中,去分辨在社会道德法典中对社会存在必不可少部分与无关紧要部分之间的微妙差异,这既是可能的,也很好理解。至少乍看起来,做出这种辨别的要求很明显,即便我们假定,只要在受到“强烈而清晰”(涂尔干)或“无法容忍、愤怒、厌恶”(德富林)的支持之处,道德法典就被法律强制。因为,所有道德约束的衰退或暴力与欺诈的任意使用不仅将导致个人损害,还将危及社会,毕竟这将剥除社会的一种主要条件,即让社会可能且值得人们之间和谐相处地生活其中。另一方面,在婚外交合问题上道德约束的衰退,或者性道德趋向于解放的总体变化似乎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亦不见得明显留下诸如“瓦解”或“人们相互疏离”这类结果。[xix] 因而,这看来值得我们停下来,考虑辨识出社会道德中被认为必不可少部分的两种可能路径。 (i)第一种可能性在于,社会不必可少的、法律强制维系的共同道德,只包括对任何人类社会的存在都必不可少的约束与禁令的社会道德部分。霍布斯(Hobbes)和休谟(Hume)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对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道德最低限度的一般特征:它们包括限制滥用暴力的规则,以及最低限度的关于诚实、守信、公平交易和财产的规则。然而,很显然德富林和涂尔干都不止于这些能在共同道德中发现并可运用法律强制执行的基础,其实任何功利主义者或沃尔芬登报告的支持者都会承认这些。很显然,德富林勋爵和涂尔干的论证都关涉不同社会中判然有别的道德规则。实际上,涂尔干坚持认为,一违反就会受刑法惩罚的共同道德可以与功利没有联系:“它们(这些禁令)在产生之时并不有用,但一旦已经持续,它们不顾自身不合理性而继续坚持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xx]适用惩罚的道德包括很多“既非关乎社会至关重要利益,又不关乎最低限制正义”的道德。[xxi] (ii)第二种可能性在于:虽然不是每一要点条目都与某一既存的道德法典有同延性,强制执行的道德不仅包括对任何人类社会的存在都必不可少的、诸如那些有关滥用暴力或欺诈等行为的约束与禁令,还包括对某一特定社会必不可少的东西。这里的指导思想是,对于任何社会而言,在其道德法典的条款中都能发现某一设定其普遍而独特之生活方式的规则核心或原则核心。德富林勋爵经常就这一方面谈问题,声称一夫一妻制被接纳“作为一种道德原则”,这当然以两种主要方式深刻普及我们的社会。其一,婚姻是一种法定制度,承认一夫一妻制作为唯一的法定婚姻形式,牵涉到相关广泛行为领域的法律:儿童的抚养与教育,有关继承和财产分配的规则,等等。其二,一夫一妻制的原则在道德上也无所不在:一夫一妻婚姻是我们家庭生活观念的中心,且在法律的帮助下已经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它的消失会带来贯穿社会的巨大变化,以至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已经改变社会的特征。 在这种观点中,对社会存在必不可少的道德既不是所有社会都要求的最低限度道德(德富林勋爵自己说,与我们社会的一夫一妻制一样,在多偶社会中多偶婚姻可能也是一种同样的凝聚力),也非及于某一既存的道德法典的每一要点条目。在此基础上它会成为一个开放性、经验性的问题,是否任何特定道德规则或禁止(例如同性恋、淫乱、或通奸)都是如此有机地联系于社会道德的核心,以至于对它维系与保存的要求被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外围工事或设垒任务。或许这种理念的某些蛛丝马迹存在于德富林勋爵而非涂尔干的论述中。但即便我们以此作为立场,我们真正面对的仍不失一种经验化的主张,即关于共同道德之维系与防止瓦解或“相互疏离”之间的联系。抛开某一特定规则是否作为社会道德核心的一项外围工事或设垒任务不说,我们现在只会面临一个单调乏味的同义反复,它依赖于一种无法涵盖社会道德整体、而只作为其核心或“特征”的社会识别,而这不是瓦解命题。 四 还需要什么,才能使上面提到的这种立场转变成瓦解命题?就是这么一种理论,在一个特定社会道德生活中维系其核心基础实际上对预防瓦解必不可少,因为这种核心道德的式微或恶性腐化是一种瓦解因素。然而,即便我们迄今已实现对某种经验性主张的确认,在构想出在经验上可验证的任何事情之前,当然还有非常多的问题要解决。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确定某种单一承认道德或社会核心道德存在的标准是什么?在现代条件下,“瓦解”与“相互疏离”指的是什么?我不会调研这些难题,然而,假如这些难题可以解决,且当这些难题被解决时,我将尝试扼要描绘那些令人信服地关乎这些议题的证据类型。这些证据类型似乎可胪列如下: (a)社会(而非个人)作为单位的粗略历史考据。这种建议是我们应当检视已经瓦解的社会,并探究在其瓦解之前是否存在共同道德的一种恶性变化。完成这一点后,我们应进一步让自身专注于共同道德腐化与社会瓦解之间因果联系的可能性。然而,我们自然也在这一点上遭遇涉及社会宏观归纳的所有常见难点,而任何试图从所谓罗马帝国衰落与崩溃中提炼归纳的人都知道,解决这些难点是很艰巨的。仅举这么一个难点:假如我们所有的证据都从简单部族社会或紧密系于土地的社会(这种似乎对涂尔干的机械团结理论而言最适于应用的社会)提炼出来,我断定,我们就不应该抱有太多的信心,去将从这些社会中提炼出来的任何结论应用于现代社会。或者,如果我们有这种信心,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成熟完善且证据充分的理论,以显示简单社会与我们社会的差异性与这些议题无关,正如实验室的规模差异性与实验室实验测试的归纳范围无关,从而可以安全地忽略。可以说,涂尔干正是这一点上尤其含糊,因为在其书中,具有广泛劳动分工特征的先进社会中仍反映于刑法的机械团结可否被忽视,他的意思不是很清楚。 (b)另一种类型的证据可从社会心理中大概提炼出来,并根据我们所设想共同道德维系方案的替代方式,至少划分为两种衍生形式。一种替代方式是在与此前由共同道德覆盖的行为领域中,实现总体一律的自由放任。例如,在双妻或单妻、异性恋或同性恋之间选择非惟个人体验问题这一观念的失效。这(自由放任的替代方式)似乎便是德富林勋爵所设想或担忧的事情,他说“社会的敌人并非错误,而是冷漠”,“不管新信念比旧信念更好还是更坏,怀疑的空档期正是危险的”[xxii]。另一种替代方式可以不是自由放任而是道德多元主义,包括有关相同领域行为的存在分歧的准道德。 对这两种替代方式导致的问题进行探究,由此出发就会发现,放弃社会瓦解的任何一般标准,即有利于支持足以近乎符合瓦解命题一般精神的东西,这才是合理的。只有我们的证据能显示,某一共同道德的恶性变化因为侵犯了看来是最低限制的要素(对滥用暴力、不尊重财产权与欺诈的禁令与约束),从而导致诸如反社会行为的总体增加,这无疑才是充分的。进而,我们才应该需要一些可确信的心理结构方面的解释,将某一社会道德的恶性衰退与反社会行为方式的增加联系起来。这里,在自由放任替代与道德多元主义替代之间,无疑存在明显的区别。在自由放任的替代中,待检验的理论可能是,处于“过渡时期的条件下”,缺乏涉及生活某方面(例如性问题)遵从共同道德要求的准则,就必然会导致个人自控一般能力的某种弱化。于是,正式被限定的性道德所覆盖的这一领域的自由放任,就会带来暴力、欺诈的增多,以及那些对任何形式的社会生活均必不可少的约束的整体失效。这是认为个人道德编织了一张无缝之网的观点。有迹象表明,这就是德富林透过“空档期”构成一种对社会存在的危险而最终诉诸的观点。因为我指责他假定道德就是一张无缝之网缺乏证据,他回应说虽然“无缝性施加了一个相当有力的比喻”,“绝大部分人将其道德视为一个整体”。[xxiii]然而,这一假定当然不能被视为显然真实的。相反的观点至少看来同样貌似真实:在生活特定领域自由放任(即便通过罔顾此前根深蒂固的社会道德而发生),可以使人们更易于顺从对暴力的约束,这些约束在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 如果我们设想“共同道德”的接替者不是自由放任,而是在一些曾被某种性道德(这种性道德已因对其限制的藐视而衰败)覆盖的行为领域中的道德多元主义,那么待检验的理论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增加了因分歧道德引发歧异的争吵,这种道德多元主义最终必将破坏对社会凝聚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限制形式。相反的理论则是,在现代大型社会的条件下,多元的道德之间完全可以很好地相互容忍。对很多人来说,也许确实是这种相反的理论在二者中更有说服力,而且,在现代生活的广泛领域中,在满口传统仁义道德的背后,有时确实存在相安无事的分歧道德。 我所做的只不过是扼要勾勒证实瓦解命题所需要的证据类型。在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这些证据之前,道德强制执行的支持者们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将观点限于保守命题,而非瓦解命题。 注释: [i] 帕特里克·德富林:《道德的法律强制》,第114页,1965。(下文引用简称德富林)“不幸的是,正如良好的社会依靠良好的道德运行,邪恶的社会可以靠邪恶的道德维系。”参见上文94页。 [ii] 这种对保守命题的特征描述引自德沃金。《德富林勋爵及道德的法律强制》,载《耶鲁大学法律杂志》第75卷,1966年,第986页。德沃金教授将德富林勋爵的工作区分为瓦解命题与保守命题,而他的论文主要关心对德富林勋爵后一说法的批判性审视。相反,本文主要关于确定需要哪些种类的证据,如果说瓦解命题不至倒塌,或被搁置而沦为保守命题。 [iii] DEVLIN 9-11. [iv] DEVLIN 10. [v] DEVLIN 10-11. [vi] DEVLIN 13. [vii] DEVLIN 10 (emphasis added). 另参见该书第9页:“任何形式的社会都由共同体观念构成。” [viii] 塔尔特科·帕森斯:《社会系统》第41页(1951)。 [ix] Id. at 42. [x]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56页(第3版,辛普森译,1964)。 [xi] Id. at 68. [xii] 边沁用整一本书致力于这一问题:什么是一条法律?什么是一条法律的一部分?什么是一条完整的法律?参见杰里米·边沁:《法理学限定的界限》(查尔斯·埃弗雷特版,1945)。 [xiii] DEVLIN viii-ix, 17. [xiv]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90页(第3版,辛普森译,1964)。 [xv] 德富林书中114页说:“当考虑对社会的无形损害时,道德信念具有重要性。只有在助长道德信念怀疑的意义上,不道德活动才是与之相关的。” [xvi]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108页(第3版,辛普森译,1964)。 [xvii] DEVLIN 18. 该书114页说:“并没有什么关于一个旧道德转向新道德的固有反感。……怀疑的空档期正是危险的。” [xviii]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107页注45(第3版,辛普森译,1964)。 [xix] 德富林勋爵在一个脚注中承认,并非每种对社会道德法典的违反都威胁社会的存在。他的表述如下:“我并没有主张任何对社会共享道德的偏离都会威胁其存在,我仅仅是说,任何颠覆活动都会威胁社会存在。我主张这两种活动都在本质上可能威胁社会存在,以至于它们都不能被排除在法律之外。”DEVLIN 13 n.1.(emphasis in original)这段话没有意指或暗示社会道德中有任何的一部分,它虽然得到愤怒、无法容忍及反感的支持,但可以被视为对社会存在不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德富林勋爵简单地使社会道德观倾向于如同一张无缝之网。DEVLIN 115.然而,在我看来德沃金教授的看法很有说服力,他认为,德富林勋爵运用同一标准(实际上是“激烈的公共反对”)去判断公共道德的背离可能令人信服地威胁社会存在与它实际上真的如此,从而去证成实际的惩罚。德沃金:《德富林勋爵及道德的法律强制》,载《耶鲁大学法律杂志》第75卷,1966年,第986、990-992页。这一点使他的瓦解命题说法缺乏经验支持。于是,按照德富林勋爵的说法:“我们必须在一开始便扪心自问是否冷静而平恕地审视,是否我们如此讨厌这一恶行,以至其仅因存在就是犯罪。如果这是一种我们所生活社会的真实感觉,我不能理解缘何否认社会有权根除之。”DEVLIN 17.但他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这些情况下对同性恋的法律容忍会危及社会的存在。对比德富林前面应用于相关淫乱问题的原则与如果“可能并不这么强烈”的情形:“这时就变成对社会危害与限制程度的平衡问题。”DEVLIN 17-18(emphasis added). [xx]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107页注45(第3版,辛普森译,1964)。 [xxi] Id. at 81. [xxii] Id. [xxiii] DEVIIN 115.
中文版《道德的法律强制》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
牛津版The Enforcement of Morals 宗教、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社会中个人自由的限制、道德领域的公私界限以及法律的介入点,这是德富林勋爵在该书中讨论的若干核心问题。 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沃尔芬登报告主张存在一个位于法律之外的私德领域,德富林驳斥了这一相反论点。不论何种情况,争论取决于公私领域的定义,而在写作过程中,德富林勋爵考察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中的教义,那是诸多论证的渊薮。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社会,所以就不再允许通过某一宗教信仰证成任何法律,尽管由于其命令与禁律的力量,道德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宗教。然而,德富林坚决主张,法律仍纯粹关乎共同道德事实,而非关乎法律应当如何的任何哲学或宗教观念。立法者应当弄清的不是正确信念,而是共同信念。那些服务于法律的人有责任保护“实然法律、实然道德、实然自由——它们并不完美,却保持其社会之既有而不至沦丧”。 辑于该书的七篇文章曾作为英国与美国的讲义发表于不同时间。然而它们都围绕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宗旨而相联,并详细考察道德律与刑法、准刑法、侵权法、合同法、婚姻法各部门法的关系。
该文原载于《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第35卷,1967年第1期,作者为牛津大学哲学研究员、法理学教授赫伯特•哈特(H.L.A. Hart);本中译版收录于德富林:《道德的法律强制》附录一《赫伯特·哈特:社会团结与道德的法律强制》,马腾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89-208页;如您观文后有所感悟,欢迎关注并分享“三会学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